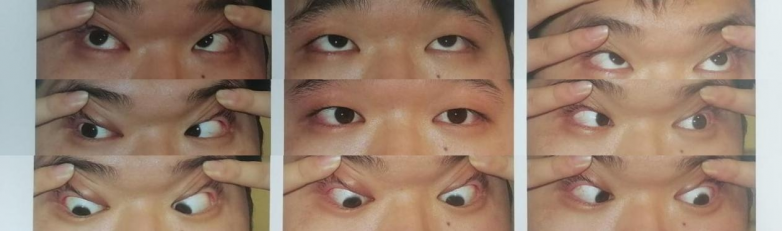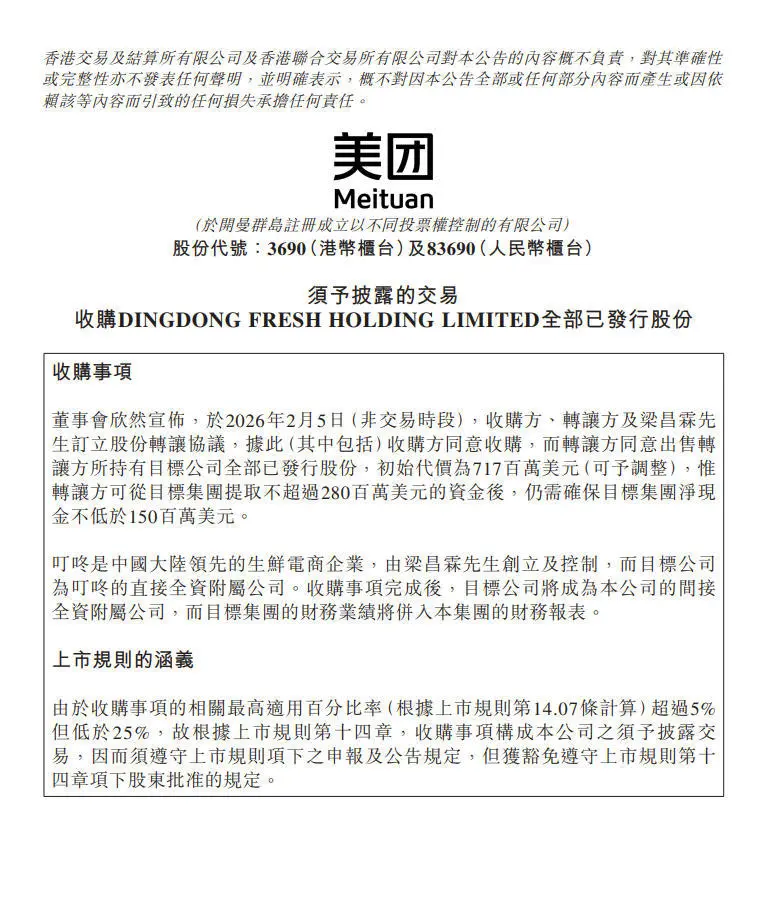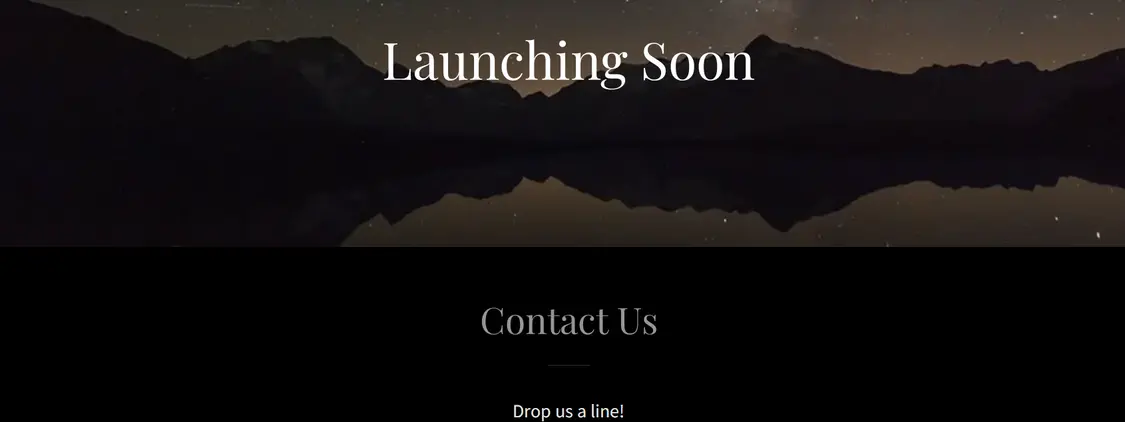3万中国人涌入非洲:种菜、做电商,卖期房
编者按:非洲之于中国的经济意义越来越大。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达29.57万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25.9%,增幅远高于其他地区。作为对比,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3.5%。预期全年对非出口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为此,华商出海产业联盟理事长卓立近期带团去了一趟非洲调研考察,以下是她对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两个非洲经济增速领先的国家的一线观察。
“在非洲,每一个时代都有富豪或者成功的企业家,但跟国家GDP发展关系并不大。所以,无论穷国还是‘富国’,总是有赚钱的机会,可以找到安顿一时、平稳落地的人生中转站。”
国内暑气当头,我决定去一趟非洲“经济火车头”——东非。
颠覆刻板印象的是,那里竟正是避暑好时候,15—25摄氏度的气温,隐隐中给非洲之行定了一个基调:非洲还是那个非洲,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非洲。

电动矿卡装载至集滚一体船启运非洲
据非洲开发银行数据:东非2025年实际GDP增速预计达5.3%,2026年预计达6.1%,均将领跑西非、南非、北非、中非。
其中,2025年,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的GDP增速或达7%,肯尼亚、南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超5%,属于“火车头中的引擎”。
我们选了有“非洲小中国”之称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及有“非洲小巴黎”之称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作为一线考察的对象城市:“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非洲,但都是非洲”,这句话将贯穿考察的全程。以下是我综合此行的一点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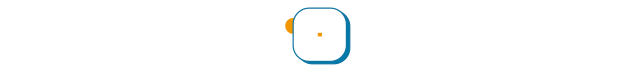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混乱与机会
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作“非洲屋脊”,平均海拔2500—3000米。或许是因为占领非洲制高点的缘故,航空业发达,往往是中国人“冒险”广阔非洲的第一站。
我们从上海浦东直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现队伍排得老长,排了足足三圈,很多人都是去埃塞俄比亚转机的,比如前往西端的尼日利亚、最南端的南非。

机场排队的人群
11个小时,一晚上时间,落地亚的斯亚贝巴。凌晨六点、13摄氏度的气温、细雨婆娑的天气,一下子将我们拉回早春。
初步印象是:尽管是非洲航运中转站,但博莱国际机场像国内三四线城市的客运中心,停车场停着的车大多数仍然是日系车,但已经有少量的比亚迪。

街边的中国新能源车
埃塞俄比亚的国土面积接近中国的九分之一,相当于内蒙。但人口达到1.2亿(实际应该更多,因为当地的统计并不那么精准),是非洲第二大人口大国,仅次于尼日利亚。
我们很容易认为,在这里,人是最有优势的生产资料,而且人口年龄中位数只有19岁,工人的平均工资低至300块人民币,加上因为自然资源优势(当地的水电、风电充沛,电力极其便宜,如果不考虑自己加投的电力设备,纯电力只要7分钱人民币一度),显然是劳动密集性产业的沃土。然而这可能造成误判。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面。我在考察期间走访了大量的市场,从当地最大的五金市场到非洲最大的露天批发市场Merkato再到当地的超市。埃塞俄比亚消费品价格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只能是“畸高”——基本是中国国内价格的3—5倍,有些甚至高达10倍,与其民众的低收入形成瞠目结舌的对比。

五金市场
原因是这个国家极度依赖于农牧业,合计占GDP的60%。比如,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大的咖啡产地。有趣的是,你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是喝不到好豆子的,原因是他们的咖啡是最大的外汇来源,好咖啡都用于外贸(但外汇依然捉襟见肘)。他们的工业基础则非常脆弱,工业品绝大部分依赖于进口,各种关税、运费等成本加上以后,不贵都难。

考察团品尝咖啡
在Merkato市场,这里充斥着大量的二手服装,很多来自中国,然而并不便宜,一条二手牛仔裤需要二三十块人民币,新货则更贵;一条质量堪忧的小毯子售价100元,在国内这个毯子大概作为赠品你也并不想要。而事实上,它们还是供不应求的进口商品。当地人走亲访友,一提卫生纸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的礼物。
因为工业稀缺,导致这个国家的失业率非常高,街道上三三两两地散站着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拿着几十块人民币的杂牌手机,失业气息浓郁。
埃塞俄比亚之所以称为“非洲小中国”,除了可以傲视非洲的三千年级的古文明史、从未被殖民的独立发展国体,核心在于它热衷模仿与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比如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制订首个“五年计划”。高峰时期,它吸引了三四十万中国人参与开拓这块“处女地”。
只是2020年开始的内战、美国取消对埃塞俄比亚的出口免税待遇、土地税收政策不稳定等因素不断扼杀这一局面,如今中国人仅有数千人。“很多人去了坦桑尼亚,那里改革开放,更包容、更有机会。”
当然,留下来的人还是告诉我:混乱而有机会。毕竟这是非洲第二大人口大国,有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有百废待兴的市场。

考察团参访当地企业
几个做工程的传统中国老板,围绕在埃塞俄比亚搞基建的中国国企做点碎石、混凝土、烧砖等周边生意,一年稳定收入在几百万至上千万元人民币,其中有个老板对我们坦言:“国内是没有我的位置的。”不少人在埃塞俄比亚娶妻生子,扎根了下来。
2023年,埃塞俄比亚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燃油车进口。一方面是其独有的电力优势,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限于外汇,靠卖咖啡,实在没有足够的外汇能够大量购买石油。由此,埃塞俄比亚一下子成了中国新能源车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市场,比亚迪、北汽、广汽都已经忙不迭在这里设厂,创造着这个国家难得的热闹。
街上那些不知道已经几手的日本燃油车,什么时候会陆续被替换成中国的新能源车,值得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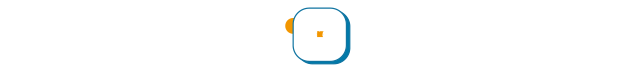
肯尼亚:涌动3万中国人的活力
从埃塞俄比亚往南,飞一个半小时,越过赤道,便是邻国肯尼亚。初步感受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
如果要从这两个国家找些共同点,可以先去被称为“东非最大贫民窟”的基贝拉看看,这里是穷困的深渊。
稠密破旧的铁皮屋像一块反复结痂的伤疤长在了离“东非最繁华现代商业综合体”GTC(中航国际内罗毕环球贸易中心)仅有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
开车送我们的本地司机在行驶到基贝拉的路程时满脸恐惧,他强调必须把窗户摇起来,原因是这里太容易发生抢劫事件,开着车窗就有人会把手伸进来抢夺。

肯尼亚街边
在肯尼亚,超市之外的蔬菜、水果都是按个来卖,因为大部分人买不起更多,只能是今天买一个西红柿,明天买一个洋葱。在一个蔬菜分发仓库里,我询问了价格,打开国内某会员超市比对了一下,如果按照公斤折算,这里的蔬菜价格与国内无异,那天的洋葱价格甚至更高一些。通货膨胀和物资的有限,让这里的大部分当地人生活仍然捉襟见肘。

肯尼亚的水果店
此外,肯尼亚的商业气氛要比埃塞俄比亚鲜活可亲得多。
尽管肯尼亚5000多万的人口规模,远不及埃塞俄比亚的一半。但人均GDP水平超埃塞俄比亚接近1000美元,普工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它即将在2025年成为东非最大经济体。
肯尼亚曾是英属殖民地,从右舵靠左开车到法律体系全部延续了英国习惯与制度,英语是官方第二语言。由此带来不少英语世界的机会。比如产生英文外呼、游戏代打行业,因人工低廉,颇受欢迎。
尤其是,无论联合国、NGO组织还是欧美公司非洲总部都喜欢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从而沉淀了一批高消费的欧美商务人群,促进产生多元化高端服务能力,有“非洲硅谷”之称。内罗毕拥有70多所国际学校就是一个缩影。
此外,四季如春的气候、举世闻名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动物大迁徙、作为非洲最大的鲜花出口国的鲜花资源,使得肯尼亚的旅游业颇为兴盛,7—9月的旅游旺季,客群爆满。

考察团观看动物迁徙
2024年中国赴肯游客数量超9万人次,较2023年增长47.4%,创下新高,2025年预计将突破10万人次。美英的游客数量更是这个数的两三倍。
所以,内罗毕的房地产发展颇为繁荣,有个中国人对我透露:“这里租售比很高,基本十年就可以回本。”具体来说,市中心的房价在8000—10000人民币/平方米,顶级的住宅能到一万五六,而一套三居室公寓月租是六千人民币左右,顶级公寓则更贵。
不少中国人在这里卖楼花创业,不少中国外派员工会买房置业,各种大小机会使肯尼亚聚集了2—3万中国人之多,数倍于埃塞俄比亚,而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实则可能更多。在这里,可以吃到地道的徽菜、川菜、粤菜。
肯尼亚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牧、旅游,工业基础同样薄弱,但是比起埃塞俄比亚则完善得多,基本的生活所需制造在国内基本能完成,中国的传音、森大等企业在肯尼亚均设有工厂,生产从手机、三轮车、瓷砖到纸尿裤等各种产品。

繁忙的工厂
用中国的制造能力在这里做一个当地品牌也有不少成功者,比如一个中国人在当地做了一个电视机品牌Vitron,43寸的价格已经打到了1000人民币左右,“在当地,海尔、海信可能都打不过它。”
一群鲜活的中国年轻创业者尤其让我记忆深刻。
一位从麦肯锡辞职的女孩在肯尼亚创业种地、卖菜,现在已经是肯尼亚最大的蔬菜采供平台。她的故事里有从三万英尺降落到地头的决心,也有凌晨三点跟着火车去卖菜的勇气。
一位新疆女孩从懵懂被公司外派到肯尼亚,到辗转到外资园区任职学习更多的跨国经营经验,她说我想要做一座桥梁,在中国和肯尼亚之间。她说,最大的难处是孤独,最能帮助成长的也是孤独,但是我看到的是她的义无反顾。
陪着我一起做拍摄采访的姑娘和她男朋友是两个90后,一个在肯尼亚做企业服务,一个在肯尼亚做广告营销。“国内父母能帮到的太多了,我想来一个遥远的地方靠自己。”
在这批年轻创业者之前,还有一批中国创业者在此扎根。前华为员工杨涛2014年在内罗毕创立了有非洲版“淘宝”之称的Kilimall,目前每日订单在20000+,24小时发货率99.95%。已经实现盈亏平衡。

kilimall仓库
新华社曾经的一个外派记者徐晖,放弃金饭碗在肯尼亚扎根创业,成立了金狮集团,生产纸张、电池等生活必需品,同时涉足地产等产业,成为在非的成功企业代表。
在此之前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一批人选择在遥远的非洲创业。我试着想找出他们在这里创业的原因,零散之中找到一些共性。
比如,肯尼亚当地四季如春的气候让很多人更愿意长期生活;作为联合国环境署、气候署的总部,以及很多跨国企业的非洲总部所在地,肯尼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商业氛围浓厚,活跃度更高,这些培育了创业的土壤;此外,基本工业的相对完善为创业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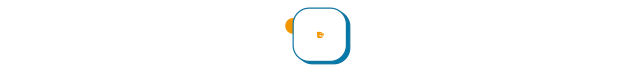
未必是中国“后花园”,
但可以是企业及人生中转站
近半个月时间的走访过后,相较于以前我对非洲的朦胧模糊看法,一些判断也渐渐清晰起来,供大家参考。
◎ 首先,非洲很难成为下一个东南亚。
这期间,我们造访了埃塞俄比亚工业部、投资局。如果对比东南亚国家相关部门,一个明显的区别现象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部门官员基本能够把政策条件说得非常清晰,每一个官员都可以报出相关准确数据。但是,在埃塞俄比亚,他们只能对着PPT模糊地讲一讲,报不出清晰的数据。原因并非不专业,更多是政策不稳定下导致的不清楚实情。
客观层面来说,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些困局。
依赖农牧业、工业基础薄弱、政策不确定、政府腐败、外汇紧缺、通货膨胀等,虽然在劳动力、关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缺点的制约明显,这一轮中资企业的供应链海外重建,非洲能承接的很可能是一批劳动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很难像东南亚一样可以承接较全的产业链。
非洲国家的发展常常是动荡式的发展,因为不同领导者的上台导致政策反复变化,加上一些内部的冲突,容易遇到“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尴尬局面,相较而言,东南亚国家总体上是属于螺旋式发展,可预期性更强。
◎ 其次,非洲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和创业者很好的中转站。
无论在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出海的中国人主流是两类,一类是大公司的海外区域负责人,一类是基础产能的制造者。前一类人的出现,源于非洲巨大的人口市场以及物资的紧缺,从酱油到汽车,非洲是一个不可忽视和放弃的市场。
而后一类人更值得我们关注,这是一批在国内其企业往往被认定为是“落后产能”的企业家,但处在非常原始的市场和极其廉价年轻的劳动力市场,它们实际上是“先进产能”。
在国内这一批创业者的知识结构与商业能力无法支撑他们顺利转型升级,在非洲却仍然可以稳健地获得一份还算可观的营收。淘汰与急需之间,需要变换的不是能力,而是市场。
就如一位大厂非洲高管跟我所说,在非洲,每一个时代都有富豪或者成功的企业家,但跟国家GDP发展关系并不大。所以,无论穷国还是“富国”,总是有赚钱的机会,可以找到安顿一时、平稳落地的人生中转站。

当地企业的仓库
◎ 第三,在非洲,先扎根、再发展是普遍的生存发展法则。
我们会发现不少非洲中国企业的发展特点是:做好一块业务后,会横向发展其他的业务。
非洲总人口超14亿,一个看似巨大的市场,但却足足有54个独立国家,是世界上国家数量最多的大洲之一,这也意味着,这只是一个看似庞大的碎片化市场。这些分散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宗教、历史、政体、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国家政策,导致难以连成一片或用一种商业模式打通,需要精细的本地化运营才能站稳脚跟。
那也意味着,每个国家的市场天花板都较低,你要重新开拓一个国家,同在一个大洲,依然需要从头开始。并且要排除掉一部分政局极不稳定和安全的国家。
同时因为经济的相对落后,消费力有限,进一步降低了单一产品的市场天花板。比如,如果你要在埃塞俄比亚做医疗相关的产业,除了需要跟印度、欧美企业竞争之外,最大的瓶颈是这个国家有限的消费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1.一个行业很难容纳很多家企业同时并存,在这里没有二八法则,只有一二三法则。
这也印证了这次考察很多非洲企业家的反馈:你要进入非洲很难,但是你扎根下来以后,别人想进入也很难。所以在这里,可能需要上演的是竞赛游戏,谁先进去谁先占领谁就赢了80%。
2.很多扎根下来的企业,均选择横向发展而非纵向深挖。
这似乎与我们管理学这些年反复论证的“多元化发展陷阱”形成了悖论,但是在非洲这个市场,这却是行之有效和不得不为的。
在我们访谈的大部分扎根下来的企业,基本都在主营业务之外涉足了其他业务,如建筑、工业地产等等,而被称为“非洲之王”的森大,业务范围从纸尿裤、洗衣粉一直到五金、陶瓷,而以手机起家的传音,则在非洲卖起了两轮、三轮电动车。
在行程考察结束之际,同行的两位企业家,一位在我们离开后继续留下来考察钢铁市场,在来非洲之前,她想的是看看动物然后回去带娃躺平,因为钢铁行业国内实在太卷了。我回国以后她给我发来信息,说:卓老师,我决定了,继续干,在非洲干,我已经在动员团队了!
另一位则是回国就开始约见出海非洲的国内企业家,“要深入再聊聊非洲的机会”“非洲让我重新有了创业的热情”。
这就是非洲的魅力,一块原始、混乱、生机勃勃的大地。这也是我们考察的意义,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发现不一样的机会。
来源 | 吴晓波频道

特别提醒:如果文章内容、图片、视频出现侵权问题,请与本站联系撤下相关作品。
风险提示:纵横网呈现的所有信息仅作为学习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一切投资操作信息不能作为投资依据。本网站所报道的文章资料、图片、数据等信息来源于互联网,仅供参考使用,相关侵权责任由信息来源第三方承担。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