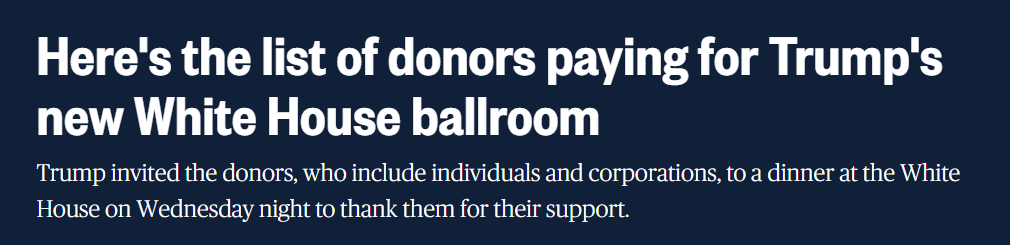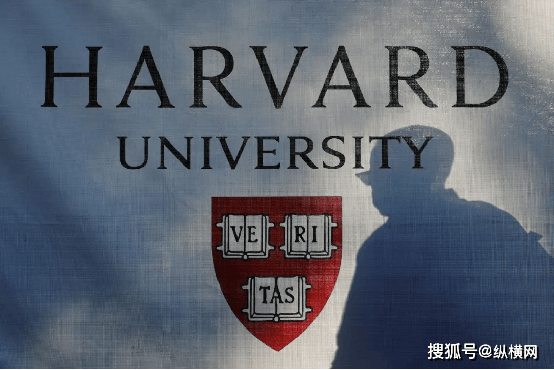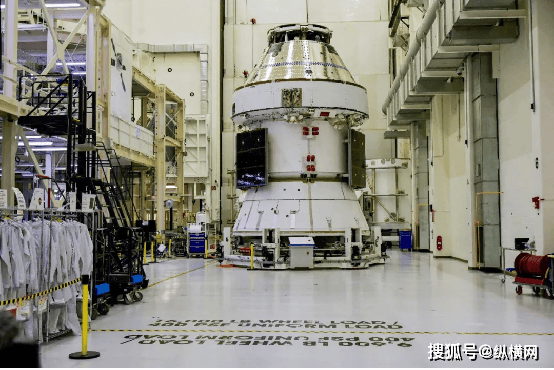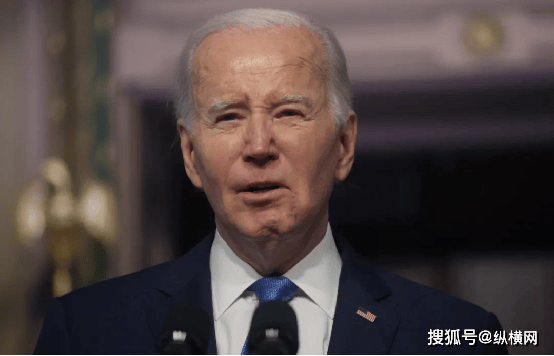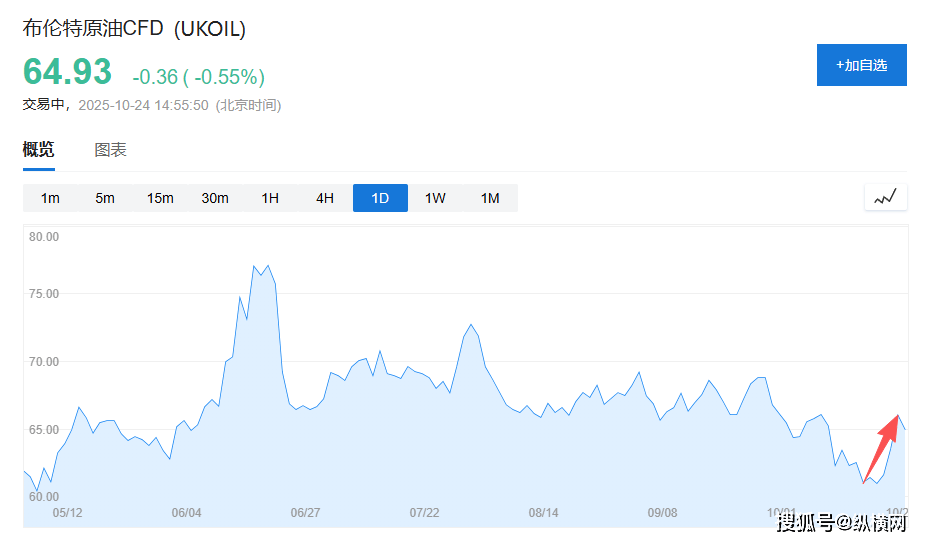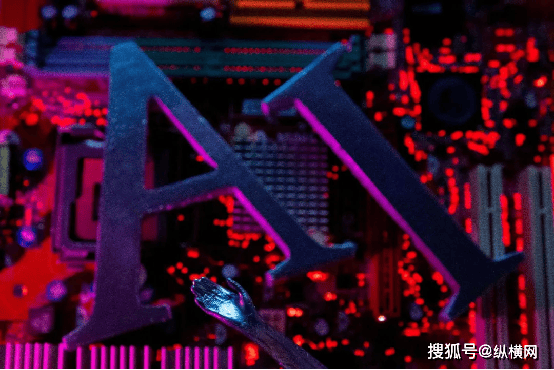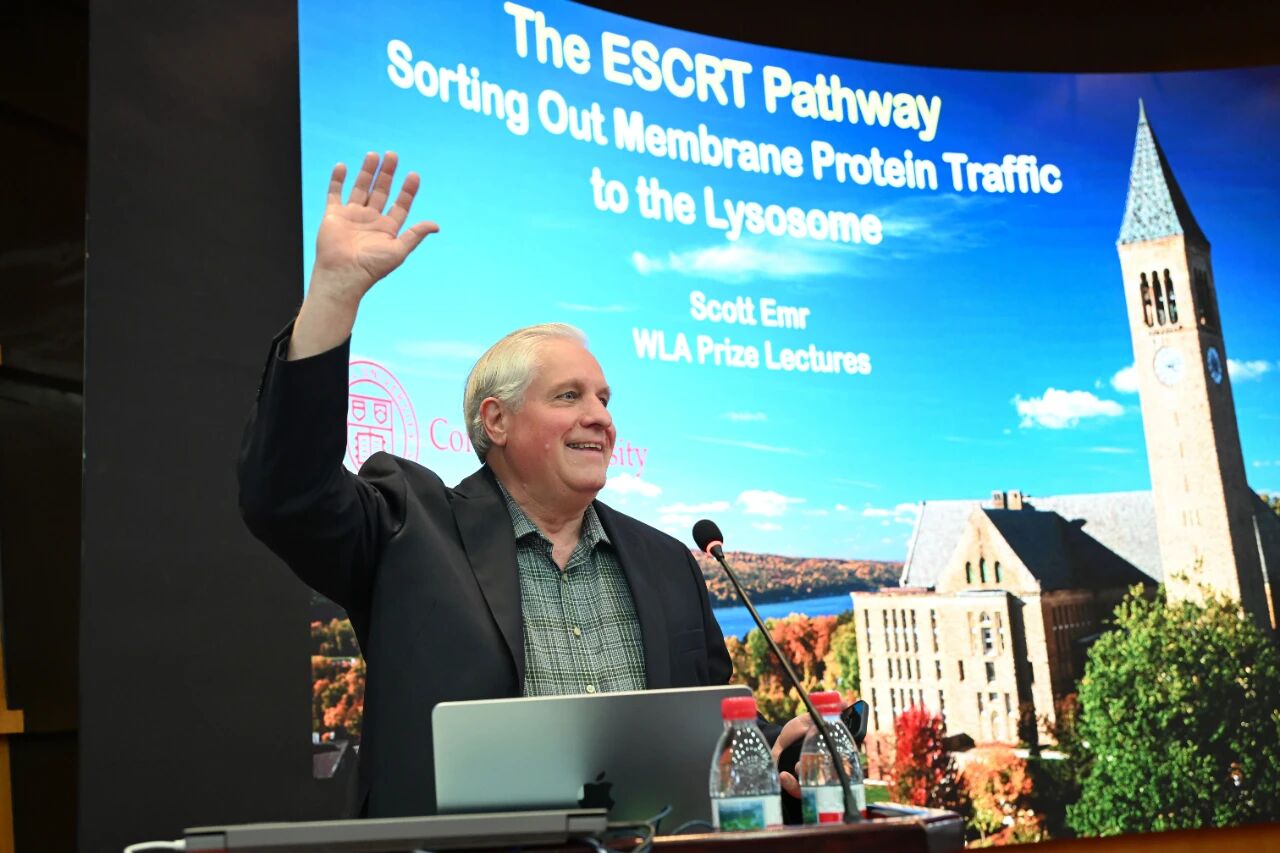致敬?仿写?抄袭?他用“晒对比”触碰文学的某个边界
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但在读书博主“抒情的森林”眼中,当代文坛的某些文本,却频频展现出令人讶异的“心有灵犀”。去年底开始,他在社交平台持续发布“文本对比图”,将多位知名作家——从斩获大奖的儿童文学作者到炙手可热的文坛新星——的作品段落,与国内外经典或已发表文本并置,揭示其句子结构、情节设计乃至核心意象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帖子如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读者的热议,也触动了业界的神经。目前,文学杂志《收获》发声“呼吁更纯净的原创”,而《花城》宣布从今年第4期杂志开始,将启用查重软件辅助内容把关。

“很开心,事情总算往前走了一步。”得知消息的“抒情的森林”对红星新闻记者感慨。此前,他被视为“一个人的打假”,在数月的历程中,经历了删帖、投诉乃至账号功能被限。
文本间的异曲同工之妙
这场行动始于一次偶然的阅读。
“抒情的森林”在阅读销量破千万、获奖众多的儿童文学《故宫里的大怪兽》时,察觉其部分片段与日本作家安房直子(《夫人的耳环》中耳环“又重又热”的描写)、美国作家柯尼斯伯格(《小巫婆求仙记》的情节)等作品存在奇妙的相似感。

常怡《故宫里的大怪兽》片段

柯尼斯伯格《小巫婆求仙记》片段
但很快,他也收到了侵权投诉通知。
系统消息显示:“收到相关权利人投诉……发布的笔记涉嫌名誉侵权”。在今年五月初,“抒情的森林”账号被投诉到无法使用回复评论功能。

在反复遭遇删帖、投诉之后,他也积累了经验,开始改变表达方式:那些激烈的措辞被替换为更委婉的“异曲同工之妙”。
并且,有着极大阅读量的他,利用查重软件和电子书网站,发现有更多的写作者的作品,存在类似的问题。
比如蒋方舟。今年将满36岁的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12岁起就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作品无数。然而,在“抒情的森林”的对比图里,多篇文章却出现了与加缪、纳博科夫等作品不同程度的相似。

蒋方舟作品与契诃夫作品对比
由此,“抒情的森林”的对比如滚雪球般扩大:从蒋方舟,他关注到其母尚爱兰的作品;阅读尚爱兰作品后,发现作家李凤群《大江边》中有尚爱兰旧作《永不原谅》的影子;继而发现蒋、李的文字里,又都有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痕迹……

李凤群作品与尚爱兰作品对比
一环套一环,文本之间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而后,在他的帖子里出现了更多作家的名字:
孙频的《玫瑰之宴》,被指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诗歌《我的手艺》、德里克·沃尔科特《安的列斯群岛,史诗的记忆片段》和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柏拉图对话中的神》有相似之处;徐衎的《肉林执》,与韩松落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有相似之处;焦典的《孔雀菩提》,与格非等作家作品有相似之处……

红星新闻:这么查下去,作为一名读者,你会对文学圈变得失望吗?
抒情的森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包法利夫人》好厉害,福楼拜好会写,加缪不愧是诺奖得主,更别说马尔克斯、契诃夫……要不然,为什么孙频、蒋方舟等等会那么喜欢他们呢?
为什么会经常“一环套一环”,因为他们所欣赏的文本类型是很靠近的。如果是好的(方向),就会致敬、借鉴、学习,如果是不好的(方向),这些优秀的经典就会像黑洞把你吸走,而在黑洞周围的人就是如此相似。
红星新闻:一些作者多年来常常在“涉嫌抄袭”的争议之中,与此同时也依然在出版著作,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况?
抒情的森林:我跟你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我曾经在蒋方舟的视频上看到她提到围绕她的争议,所以她本人肯定是知道并在意的。
对于他们来说,“回旋镖”总有一天会来的。你只要是白纸黑字的公开出版物,我们就是可以找到的。
要“公开”,不要“私信”
但没有谁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如此相似”的拷问。
于是,有的作者或编辑通过私信联系,也有的通过第三方转述“意见”。在他的主页评论区,不少网友目睹了蒋方舟从“关注”到“取关”的全过程。
“抒情的森林”回忆,在发布了几篇涉及蒋方舟作品的讨论帖后,其中一篇帖子显示“相关权益人投诉”后被删除。随后蒋方舟关注了自己的账号,“(她)就过来找我,说是她投诉的,不好意思。”
据他透露,后续私信中,蒋方舟一方面称是“早期不成熟作品”,表示“理解和虚心接受”;另一方面希望交流,“认同较真行为”,探讨文学。
但“抒情的森林”觉得奇怪:“写《主人公》时已经是一个三十好几的人了,她写了20多年了,还不成熟,这说得通吗?”


蒋方舟《主人公》和卡达莱《梦宫》的对比
他总结许多私信的潜台词是“求放过”。
有些甚至让他感到分裂,“有一位编辑发来私信,先是表示感谢,‘以后多提醒’,片刻后再发来消息‘这个可否拜托先删一下?’”
不久前,孙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感谢“抒情的森林”指出了自己早期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当年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对福楼拜十分痴迷……在写作时会有意无意地把一些自己喜爱的句子带入小说。”

对此,“抒情的森林”的评价是“坦诚,但又没完全坦诚”:“她只承认福楼拜,是我发了福楼拜;后来我发了严歌苓、钱钟书、朱天文……你要挨个道歉,还是挨个说‘我对每一位作家都喜欢到倒背如流,并不自觉地用在自己作品里’?”
红星新闻:你在帖子里写,请作家、编辑不要给你发私信,为什么?
抒情的森林:(他们)跟我没关系,你写出来的书是卖给读者的,是公开发表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告诉我你的心路历程如何,你背后有什么苦衷。
同样的道理,我认为作家不应该跟读者建立私人联系。他们要做的事情是给读者一个交代,而不是找我私聊,让我不要做这件事,有什么话就公开说。

红星新闻:你希望他们给出怎样的反应?
抒情的森林:我从没有期望或奢求他们做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为我的期待去干嘛。作家也好,出版社也好,编辑也好,一部作品被指出这种问题的话,他们是有义务要做出回应的。不是对我,是对读者、对公众。出现这种事,作者、出版社等相关责任方应该都有相应的应对机制。
红星新闻:有一些特别年轻的作者,有争议的作品是首作。你觉得大家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吗?
抒情的森林:当然是给机会。但不是我给,而是这些刊物会不会给发表机会,以及曾经对他们失望的读者要不要再买他们的书,这是读者的自由。
有一些作者跟我说,写作对他们非常重要。但我觉得,写作是有笔有纸有思想就能进行的行为。你再怎样被大家“抛弃”了,你依然可以写的。你这样说是真的热爱文学吗?你背后的潜台词是你不想失去现在的光环,不想丧失发稿的资源。
“长脚”的帖子,会去到该去的地方
各类超出预期的反应,让“抒情的森林”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正在向某个边界触碰。他知道,虽然很多编辑、作家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有在看他的帖子。
在最初发布“文本对比”帖时,“抒情的森林”还会@相关方,希望可以借此提醒他们看到。时间一长,他发现,其实无需提醒,文学圈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圈子,这些帖子会“长脚”触达它该去的地方。
至于这些问题最终能否得到回应、会以什么形式回应,他并不抱确定期待,“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我可以控制这件事要不要说出来,我说出来的东西是否客观和有道理,以及大家是否也认为这件事有道理、值得说,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动力。”

红星新闻:有些网友会说,被指出的作者只是模仿了其中的某一段,但整篇文章还是作者自己写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你认为致敬、仿写与抄袭的边界在哪里?
抒情的森林:这确实是争议的核心,但对我来讲从来不是问题。抄袭确实可以用法律判别,但如果因为大家觉得只要不违法就OK,那其实是一种对写作伦理的退守。对于一位作者而言,和另一位作者可以有几十字、几百字一模一样,这说得通吗?
“致敬”的例子很简单,就像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的《1Q84》,你一看就知道是致敬《1984》。他是会特意让人一眼看出来。
没有哪个作家不是通过学习别人的作品来写作。但到自己创作小说时,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边界。文学创作是非常具有个人化的,不可能有两位作家相似到一模一样的程度。任何对创作有尊严、有抱负的作家,是会以和别人的文字相似为耻的。

红星新闻:在帖子发出后,一些作者和期刊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你如何看待?
抒情的森林:有作者通过别的博主联系我,说因为我发出的内容抑郁了,或是上来就晒病历,告知我“这件事如果持续下去,病情会急剧加重”。所以我说不要私底下交流,这很容易变成诉苦和道德绑架,变成说“你要害死我,你让我抑郁”。
但是,这些压力真的跟我们做的事情有直接关系吗?这些压力不是我给的,应该是千千万万个读者给的。阅读这件事,本来就是作者跟读者的共谋。作者创作出好作品,读者买来看书,喜欢就夸奖,不喜欢就指出来,双方应该是这种流动关系。你要说“压力”的话,创作也有压力,发刊也有压力,编辑给的意见也有压力,那凭什么到了最普通的读者这里,给出的意见就成为“巨大的压力”?
红星新闻:在整个过程中,你会有“独自抗争”的感觉吗?
抒情的森林:并不会。我始终针对的,还是作家创作的作品。我也希望大家说话有理有据,尽量讨论作品本身。但我相信,作家还是要面对自己写的东西,面对他的读者。我属于真正的读者,会去认真地看他们的作品——可能莫言看焦典的小说,都没有我看焦典的小说看得认真。
我并不是一个拿着放大镜在故纸堆中找别人漏洞的人,我只是一个看书的人。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仍然渴望阅读优秀的作品,仍然渴望看到好的东西。不要觉得我在针对他们,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对年轻写作群体永远抱有期待。
红星新闻记者 | 毛渝川 任宏伟
编辑 | 蒋庆
特别提醒:如果文章内容、图片、视频出现侵权问题,请与本站联系撤下相关作品。
风险提示:纵横网呈现的所有信息仅作为学习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一切投资操作信息不能作为投资依据。本网站所报道的文章资料、图片、数据等信息来源于互联网,仅供参考使用,相关侵权责任由信息来源第三方承担。
本文地址: